界面新闻记者 |
界面新闻编辑 | 姜妍
2007年夏天,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亚历克·阿什(Alec Ash)第一次来到中国,在青海的一个藏族山村支教。三个月里,他背着包走访了许多城市,从香港地区到成都、北京,他随身带着美国旅行作家保罗·索鲁的《火车大巴扎》和《在中国大地上》两本书,脑海中幻想着马可波罗式的壮游之旅。在此之前,亚历克在大学修读英语文学,对中文一窍不通,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在他眼中就像一个“巨大的谜团”,他忽然很想要了解这个国家及其背后的文化。
一年后,亚历克回到中国,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接受中文培训,并定居下来。一位中国朋友给他起了个中文名:艾礼凯——这与他的英文名发音相似,并且有“礼貌”和“成功”这两个寓意,他很喜欢这个名字,一些朋友就叫他“小凯”。
此后十余年,艾礼凯先后生活在北京和云南大理,直到2022年离开。如今的他可以说是一位“中国通”,他在文章里自如地引用中国古典文学段落,或是列举鲜为人知的民俗与地理知识;生活中,他熟练地用中文与人交谈,拥有超过3000个微信好友。
与十八年前的初印象相比,中国社会早已发生巨大变化,这些鲜活经验始终吸引着艾礼凯,到目前为止,他出版了两部关于中国的书籍,并在英文媒体主持中国观察专栏,美国作家何伟(Peter Hessler)称他为“天赋卓绝的当代中国观察家”。


上海书展期间,艾礼凯带着新书《大理一年》回到中国,这本书记录了他离开北京、移居大理的故事。在书中,他书写了一个个像他一样从城市逃离、试图在村庄隐居的人,他们过着平静而丰富的生活,却也面临着各自的心灵困境,他试图透过这些故事追问:逃离真的能使人获得自由吗?
在与界面文化的对话中,他多数时候使用英文,有时又会因为更准确的表达而主动切换回中文。在他看来,说英文的亚历克·阿什和说中文的艾礼凯有点不同,就好像他在努力变成全新的人,这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: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,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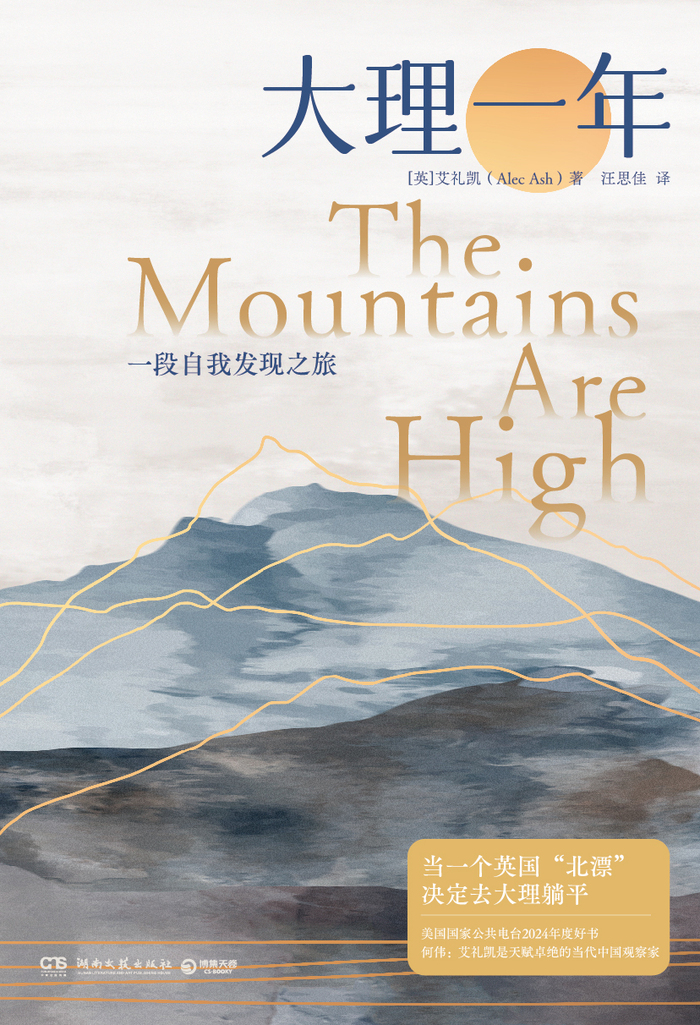
[英] 艾礼凯 著 汪思佳 译
博集天卷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-8
01 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令人澎湃
在《大汗之国》一书中,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写道:“几世纪来,流行风潮的无常,政治情势的改变,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,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完全消失过。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,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,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,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。”
2001年,何伟在美国出版《江城》,这本书记录了1996-1998年间他在长江边的小城涪陵教书的经历,世纪之交,中国社会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,何伟捕捉到这些飞逝的重要时刻中更持久、更贴近人心的东西。《江城》获得了很好的反响,很多西方大学将其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指定书目,也是在这一时期,西方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新的高峰,陆续有人慕名来到中国学习或生活,艾礼凯就是其中之一。
抵达北京的第一周,艾礼凯在鸟巢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。在他的记忆中,那段时期“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。”他如饥似渴地感受着这一切,北京规模之大、节奏之快,令人心潮澎湃、兴奋不已,就像二十多岁的他自己,仿佛一切皆有可能。
艾礼凯很快见到了时任《华尔街日报》驻北京记者的张彦(Ian Johnson),后者在中国生活近20年,出版有《野草》(Wild Grass)、《中国的灵魂》(The Souls of China)等作品。在那段时期,有许多外国记者和作家生活在不同城市,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和书籍,比如欧逸文(Evan Osnos)、梅英东(Michael Meyer)、史明智(Rob Schmitz)等人。艾礼凯也开始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,并梦想着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作家。
在北大读书期间,艾礼凯认识了许多同龄的朋友,并对80后这一代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他开始写一个名为“六个人”(Six)的博客,记录这些中国朋友的故事。这延续到他的第一本书《许愿灯》(Wish Lanterns),在书中,艾礼凯选择了另外六个不同的年轻人,包括务工人员、企业家、流行歌手、网民等,试图覆盖更多元的背景,他花了2-3年时间与这六个人相处,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史。在他看来,年轻人就像是楔子的细端,正通过代际和社会的转变慢慢撬开中国,相比于在运动中成长的前一代人,新的世代正在变得更开放,并开始持有许多新的观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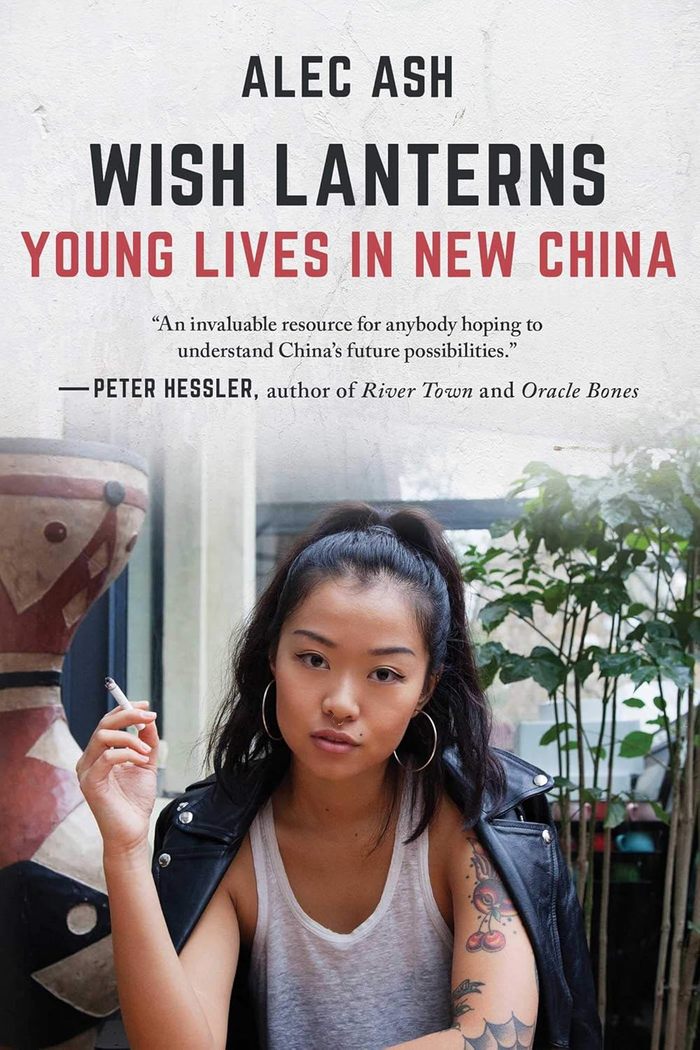
Alec Ash
Arcade 2017-3
此后几年里,艾礼凯曾主持过一个名为“蚁丘”(the Anthill)的中国写作社群,也远程为《洛杉矶书评》编辑中国频道。当被问到自己与其他中国写作者的不同之处时,艾礼凯说:“我没有他们那么有名。”他喜欢称自己为“最差的那一类记者”,因为他更关注文学性,试图在观察记录的同时捕捉语言之美。随着阅读与生活的深入,他反而意识到,自己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,对中国的认识就越少,“因为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更多需要去了解的地方,比如地理和文化上的多样性。”
02 逃离城市,过一种“自然生活”
2017年左右艾礼凯在东城区某条胡同的家也面临拆迁,他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陌生,生活乏味、一成不变。
那段时间,他经常在朋友圈看到移居大理的朋友发出的照片,这让他感到羡慕,那里气候宜人,风光如画,被戏称为“躺平之都”,也有人将其类比为“大理福尼亚”。他对大理的闲适生活心驰神往,同时也对这背后的社会变迁产生好奇: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奋力挤进社会上层,可如今这种归隐田园的趋势与以往的城市化进程截然相反,这是为什么?
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状况。早在工业革命后,英国就出现了类似的回归农村运动。艾礼凯尤为好奇,中国如何在短短50年内经历了英国社会250年的转型过程,这背后的问题是,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到了什么阶段,人们对生活的观念及想象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?
2020年1月,艾礼凯正式搬到大理,他在苍山脚下租了一间院子,开始自己的隐居生活。在大理的一天与北京非常不一样,艾礼凯并没有固定的工作计划,他在网上兼职教英语,也从事写作,其余时间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做饭、种菜、射箭,他收养了一只名叫月亮的小狗,会一起在苍山的小路上跑步。这正是许多人来到大理的原因:这里没有996,可以充分享受生活。

艾礼凯回忆,在北京的时候,他的一天会有大量时间花在地铁上,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。而在大理,很多地方仅凭走路或骑车就能抵达,“感觉我周围的空间变大了。”他平日喜欢在村子里闲逛,跟邻居们聊天。在今天的中国农村,即使是大理这样历史悠久的西方背包客目的地,外国人的面孔仍然是一件新鲜事,他总会引来村民的注视和议论,也会受到热情的礼遇。
在大理,桃花源和香格里拉的幻想总是被提及,许多人对大理生活有一种隐居者的浪漫化想象,“大理,就是大的理想。”艾礼凯认为,这种回归自然、返璞归真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,而这正呼应了今天人们厌倦大城市的灯红酒绿,向往田园生活的愿望。
艾礼凯发现,大理最突出的生活口号就是“自然生活”——既可以是“亲近自然”,也可以解释为“顺其自然”。这是一种不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或成功的潮流,他认识的不少人都是辞职来到大理,享受着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,不再给人打工,而是自己掌控生活,比如运营自己的农场、客栈或新式学校。英国农学家约翰·西蒙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《自给自足生活简明指南》在新大理人之中很受欢迎,人们拥抱环保主义,抵制那些让民众与农耕生活脱节的社会工程。
但另一方面,城市生活似乎又是难以摆脱的,人们在抵制城市化的过程中,也在逆流而行:移居者憧憬田园诗般的完美乡村生活,但他们带来的资金流却正在把这里变成另一番模样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,大理的农村正变得“小资”,高档度假酒店不断被建起,房价、物价乃至服务业都因势抬价。在艾礼凯看来,大理城乡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:这里既不像乡村,也不像城市,更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。


另一个难以摆脱的是数字技术,尤其是智能手机。许多人来到大理后发现,自己还是要依靠现代社会的种种设施,比如网购各种生活用品。也有人在追求田园生活的同时,陷入了矩阵世界——在网上晒自己虚假的幸福生活。某天,艾礼凯意识到自己对手机上瘾了,即使身在大理,他每天仍然会花上数个小时使用手机,他拼命想要戒掉手机瘾,却也渐渐明白,看手机很多时候是为了分散注意力、麻痹自己的精神状态,他来大理是为了逃离城市,但不能逃避自己的内心。
03 一场“向内看”的心灵革命
来到大理之前,艾礼凯就已经在脑中计划写一本新书。最初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观点,只是想知道,这些人为什么选择搬到大理?他得到的多数回答是:为了自由。
什么是自由?艾礼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他认为,随着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,人们能够通过财富来决定自己的人生。但与此同时,大城市中,不同年龄的人们即使已经拥有了经济自由,有一定存款,体面的工作,他们中的不少人仍不开心。
艾礼凯认为,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产生了怀疑。在第一本书《许愿灯》中,他笔下的年轻人还怀有更大的梦想,从农村来到城市,认为只要自己考上大学,留下来找到好工作,就能取得成功,“当时有一种感觉或希冀,就是他们真的能变得有钱,许多人都想成为下一个马云。”如今,在全世界范围内,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变小了,年轻人发现城市经济不再能够给予他们进一步成长的空间,机遇在减少,生活成本也在提升。
这关联向当下人们更大的内心问题:自然状态往往就是焦虑和紧张。在大理,一位从上海移居而来的心理医生对艾礼凯说,焦虑已经成为了一种人们普遍的状态。

过去几年,大理成为了实践“躺平”这一生活方式的重要场所:有人躺在家里从早睡到晚,有人抽烟、画画、照料花园打发时光,也有人出家做了僧人,终日打坐冥想。
在艾礼凯看来,这些实践都反映了越来越多人开始试着“向内看”——将目标从经济发展转向个人发展,甚至灵性发展。相比于崇拜成功和财富,人们更想要发掘内心的资源,来让自己过得更幸福。
英国哲学家以赛亚·伯林曾对“积极自由”和“消极自由”作出经典的区分,但在艾礼凯看来,他更想要讨论的是“内部自由”与“外部自由”:多数人思考的都是外部自由,比如人是否能自由行动、拥有权利,但在大理,人们对内部自由更感兴趣,它可以是灵性层面的自由,也可以是对社会的某种逃避,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
艾礼凯观察到,大理也正在发生着一场“心理热”,他在书里写道:“我们都在大理寻找这样的东西:一个有归属感的聚集之处、一颗信仰的种子、滋润心灵的甘露。”
与中国其它地区一样,大理也掀起过一股心理治疗的热潮。艾礼凯在书中记载了一家规模庞大的疗养院,被形容为“大理的魔山”,他们会为客人提供一系列疗愈服务,包括现场瑜伽、水疗、心理咨询等。此外,大理还存在各种个人发展出的灵性修习方式,比如一位叫“梦隐士”的人开发出了清醒梦的训练课程,帮助人们透过梦境来探索自己的内心,也可以在梦中发泄压抑的情绪。

在艾礼凯看来,这些种类繁多的修习背后,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,那就是寻找某种内心的平静。这同样是需要投入的,要“努力做”,比如每天长时间的冥想。这里似乎也存在矛盾:城市生活中对“努力工作”的强制追求让人们陷入精神危机,但要想摆脱这种危机,同样需要在灵性实践中付出努力。但在他们心目中,至少这是自己选择的生活,自由可以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能力。
04 不安情绪让人们涌向大理,也让他们重返城市
这场逃离会有终点,在大理,不少人在一段时间后选择了离开,“对很多人来说,大理生活更像是一场实验,很多人都失败了。”
艾礼凯始终认为,经济自由是最大的自由,在大理也是如此。许多人带着远离社会、低成本生活的幻想来到大理,却发现大理的房价、物价也在不断上涨,而在此赚钱却很难。在大理有许多数字游民做着远程工作,但这仍是少数人才有的能力,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种工作机会,其余的人或是依靠存款,或是过着嬉皮士一样的低物欲生活。
于是,当生活重压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时,人们就会选择离开,去寻找物价更低的“下一个大理”,或是回到城市,找一份挣钱的工作。艾礼凯在书里写道:“不安情绪让逆向移居者涌向大理,但也是这种情绪,最终让他们重返城市。”

艾礼凯也离开了。2022年10月16日,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从苍山俯瞰大理古城的照片,房屋像鱼鳞般排布在田野间,远处是平静的洱海。他写道:“大理大理,下次见。”他将要结束三年的大理隐居生活,去往美国,做回那个亚历克·阿什。
在此之前,包括何伟在内的许多外国作家都离开了中国。在亚历克心目中,何伟是这群作家里写得最好的,未来也很难有人能够超越。在他看来,何伟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欢迎,背后反映的是中国读者仍然渴望看到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,“像是照镜子,透过他人的目光来看自己。”但他并不确定今天是否仍是如此。
亚历克认为,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已经没有二十年前那样强烈——这或许也因为西方社会自身的问题正在加剧,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。这造成的结果就是,在当下,尽管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,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却变得越来越少,国家之间的流动,不论是人口还是文化上的,都在减少,“就像生活在彼此的泡沫里。”
在一篇题为《场边汉学》(Sideline Sinology)的文章中,何伟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报道生涯,以及在今天进行这些报道的种种困难,他写道:“在某些方面,比如捕捉日常生活的质感,没有什么能替代亲自身处中国。就这一点而言,我们已经进入了‘场边汉学家’的时期。”

在美国,亚历克发起了一份新的英文刊物《中国书评》(China Books Review),并担任主编。他开玩笑地说,自己现在是“扶手椅旅客”(armchair traveler)——只是坐在家里阅读中国相关的图书,写作书评。他认为在旅行很难实现的当下,阅读是一个很好了解彼此的方式,不论是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写作,还是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写作。
因此,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更像是打破这些泡沫。这在当下变得更困难,在美国,他所在的书评媒体会举行许多线下活动,介绍中国相关的图书,但他注意到,尽管目标人群是西方读者,但来到现场的听众很大一部分仍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——从这个角度看,泡沫仍然存在。即使如此,亚历克仍然表现出一种乐观,“我这辈子都会是中国的观察者。”他笑着说。
(文中图片除标注外,均由出版方提供)








